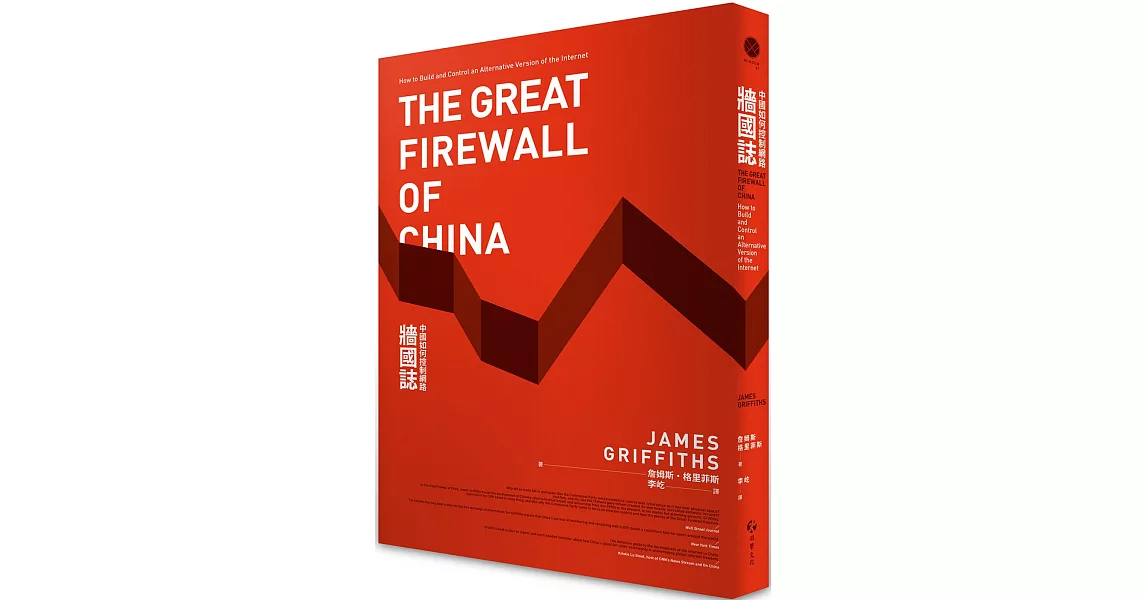本文為遊擊文化出版的《牆國誌》譯序。
「街壘」一詞出現於十六世紀最後三十年,有個替法國王室打胡格諾教徒的軍頭,在戰事中被打爛了半張臉,那顆子彈發自戍塔底下的街壘。此後,尤其在十九世紀前半葉,以大型器物阻斷蜿蜒狹窄的城市街道的街壘,讓議會的先生們難以赴宴,消息散亂,政府鎮壓的武力也容易被分化。街壘成了起義的象徵,昭示街坊齊力抗爭的決心。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,城市街道拓寬,工業區的發展使勞動人民長途通勤,城鄉移民和都市更新沖散了老街坊,更別提大型家具等市民容易取得的素材,在坦克面前都不是障礙,一概碾壓、炸毀,於是街壘在二十世紀迅速沒落。
街坊換成平台,坦克換成鈔票,那麼街壘的歷史差堪比擬美國主導的網際網路發展。起初,小網站林立,互通聲氣,形成站群。繼而目錄(如草創時的Yahoo)、關鍵字搜尋(Google)、社交圖譜(Facebook)和內容(抖音)等「梳理」網路的方式各領風騷,在在顯示組織與詮釋資訊的商業價值。譬如對搜尋引擎來說,曾盛極一時的郵件名單、BBS和論壇都如同街壘,搜尋引擎對其內部情況若非一無所知,情報也很局限。
假若一個新服務成功煽動用戶湧入,而且還能留住人,那下一步通常就是拉牆,闢護城河,設立事務窗口(API),留住可套利的資訊。
在中國,政治凌駕一切,維穩優先。根據本書的報導,天安門事件前兩年,中國首度接上網際網路,九年後,總理李鵬簽署第一九五號國務院令〈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〉,標誌「牆國」策略成為公開的遊戲規則,中國政府要窺看從網際網路進出全中國的資訊,牆內必須透明。
接下來十幾年,防火長城維穩成效甚佳。本書記錄了法輪功人士、流亡藏人、維吾爾人等各方與長城鬥法的故事,以及網路公民社會的街壘一一被清場的始末,這部份也是二○一六年,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,輿論逐漸「有感」的面向。牆內牆外的差異不再只是臺商、臺幹親友的入境隨俗,而是出征蔡英文臉書帳號的五毛、小粉紅「平行時空」的言論。
「牆國」審查網路資訊這一面,很容易讓人感受到制度差異,進而上綱到文化、民主、自由等價值差異,本書對此多有著墨,在此不贅。值得注意的是,網路從處處街壘變成眾巨人的圍牆花園,就「圍牆」促進資訊產出,還有篩選、扣留資訊而言,並無二致,只是對公司而言是經濟利益,對中共而言主要是政治利益。當然中國、俄羅斯等威權國家之外,我們還能跟巨人談隱私,但隱私跟使用資訊服務的舒適、便利,大抵會是恆久的拔河。即使不給 Facebook 個人資料,你也沒辦法隱去你的帳號跟其他帳號的關係,畢竟社交圖譜是該公司的生財之道。
其次,在網際網路上束起十四億人口產生的資訊,讓中國得以豢養自有的資訊科技生態系,讓魯煒這種貨色成群結黨來尋租(參見本書第六、十五、二十等章)。審查網路資訊有其產值,是許多人的工資所繫,這是防火長城的經濟功能。尤其對佔中國人口九成的漢族來說,其他民族能否在網路上發展、延續其文化,恐怕很難當一回事,遑論迫害的相關資訊往往是被屏蔽的。
此外,中國多方滲透多邊主義的組織,外銷牆國之道,本書記錄了二○一二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(第二十章)和二○一四年世界互聯網大會(第二十一章)的始末,以及(主要是美國的)公民團體如何與之對抗。幸或不幸,武漢肺炎爆發後,中共在國際上的信用和國內的正當性都大打折扣。世人或許會逐漸認識到:僅限於有領土和武力的主權國家參與的俱樂部,未納入非政府組織的多邊主義,不見得有多高明——畢竟網路主權學說太迎合主權國家治理人口、維護政權的需求,中共更已準備好將全套技術輸出。
《牆國誌》記錄了街壘被打穿的歷史,然而,就如同街壘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晚上、巴黎的給呂薩克街重現,在香港雨傘運動、反送中運動重現,群眾的資訊素養也會與審查機制共同演化。推陳出新的翻牆工具和本書第十八章提到的敏感詞鬥法,都是例子——當然,我們可能過度關注線上的情況了。